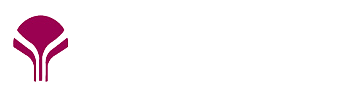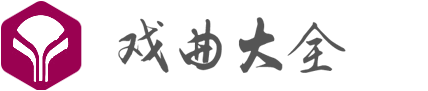扯锯拉锯姥姥家唱大戏之二//曲剧《卷席筒》:小仓娃是个怎样的少年
李小是 罗陀思花园
一、
曲剧《卷席筒》,对我一直是个谜。
小时候,关于这个戏的记忆是这样的。先是大人们常常手舞足蹈地唱来,一段又古怪又好听又好笑的戏文:“我把这前前后后,左左右右,曲曲弯弯,星星点点,给你一块往外端呵。”
待见到舞台上,一个扮丑的男人如是唱着,黑黑眼圈白白鼻子红嘴唇,蚯蚓一样长的眉,还扎了冲天小辫,有趣得很哪。
但他越唱越急,本来就听不懂的戏词更听不懂了;唱得浪花翻滚,最后张开了手臂,“我的大老爷啊!你看我浑身上下,上下浑身,都是冤哪。”这句我可牢牢记着了。那“啊”拖得好长,像打了结的绸子甩啊甩,而我奶奶,我妈,家里的女人们,哎,不只女人们,早就眼泪花花,小手大手地,抹起眼睛了。
再大点我知道他唱的是“登封小县”的小仓娃,大人们爱得不行的这演员是曲剧名丑,叫海连池。妈妈没有像《打金枝》、《对花枪》、《朝阳沟》那样给我掰开揉碎讲它的戏词,它就在幼年的记忆里成了谜:我以为丑角都是好笑的,为什么它这么催泪。
二、
三十岁之后重新看戏,我终于知道了《卷席筒》(1981西安电影制片厂版)是怎么个故事。
登封县的一个财主曹林,续弦赵氏,带了个油瓶小仓娃。赵氏思谋赶走曹林的长子曹保山,好为小仓娃占下家产。小仓娃却瞒着娘回护哥嫂。这年曹保山上京赶考,小仓娃偷偷送他盘缠,为他照顾嫂子和一双小儿女。赵氏看小仓娃愚憨不通,就使个计支开他;再使个计送汤药送曹林一命归天,祸嫁儿媳,贿赂官府,给她下了大牢。小仓娃带着金哥和玉妮儿去探监,无奈之下击鼓鸣冤,称“后老儿(后爹)是我害死的,为的独占家产”,就此替嫂子坐了牢。压赴洛阳上法场的“仓娃起解”,也是父母辈多会唱的一段:“小仓娃我离了登封小县,一路上受尽饥饿熬煎”,他不舍的,是与侄儿侄女玩耍的好时光;而嫂子赶来送行,小仓娃嘱嫂嫂“我死后你买条芦席把我卷,扒个坑埋了就算完”,乃是这戏名“卷席筒”的由来。
当然,小仓娃没死,洛阳审他的钦差正是中了状元的哥哥曹保山。观众都知结局,但背对“大老爷”的小仓娃开口,“大老爷你稳坐在察院,我把这前前后后,左左右右,曲曲弯弯,星星点点,给你一块往外端”,一段曲剧特有的长叙述,配着曹保山在身后强抑的悲辛动容,人们总是听得看得热泪滚滚。
“大团圆”的喜剧表达才新鲜:小仓娃“挺尸”法场,嫂嫂抱着芦席哭而后卷;小仓娃几番从席中溜出,引得嫂嫂大惊活见鬼……
我解了小时候的惑:它确是喜的,也确是悲的。那泪中的笑来自小仓娃的憨,藏于憨中的大智,来自对世态的戏谑、官府的嘲讽;那笑中的泪来自人们在小仓娃身上寄托的“无条件的仁义”,来自无视金钱、超出血缘的人间情,也来自那“芦席一卷”所象征的百姓的命!“卷席复生”的结尾,确是来自生活经验而超出其上的艺术创造,带给人们欣幸的滋味是复杂的:芦席是苦命、也是人们相互救助、相互承担,并从中复生的见证。
我惊艳的,一是丑角主导,一是“小仓娃”这个少年丑角,不是滑稽的丑、逗乐的丑,而是憨的丑,让人心疼的丑。生于1941年的海连池拍这部电影时候年近四十,唱作俱佳,举手抬足无不有戏,却不是仰赖声音和形体的夸张,而毋宁更有赖于其拙、稚气可掬;他模样不是少年,但那无辜的、闪亮的眼神,全然是少年!
但又有了别的惑。
这个戏据说源自清末一个潦倒的秀才周任,百年来各种地方戏班把它“拉面条”——故事衍生故事地成了连台大戏,又有名《白玉簪》、《三贤传》、《斩张苍》等。早年这种特别乡野的地方戏都是“活词”演出,没有剧本。但2006年洛阳曲剧团排《卷席筒全传》十集,自云以老艺人流传的《白玉簪》为本,从中可以窥得早期模样:原来贯穿线索,是嫂子张氏;作为反面人物特别“有戏”的,是好吃懒做、贪心狠毒的赵氏。故事背景是安史之乱,逃难路上杨贵妃把与唐明皇的定情之物白玉簪,交与宫女张风莲;张凤莲被外出做生意的曹林救回河南老家,遂有了保山娶亲、蜜蜂之计、赶考献宝、赵氏下毒、仓娃坐牢的连串故事。《白玉簪》曾是包括豫剧在内的许多地方戏的剧目,建国前后,则成了曲剧丑角老艺人的招牌戏——具体演变过程难考,但至少可知附会帝王家的奇情故事《白玉簪》,是逐渐演化为小仓娃为主角的《卷席筒》的。这是否与曲剧较之豫剧更“土”、更多表现人情伦理的特征有关呢?
#p#分页标题#e#发源于河南临汝地区的曲剧,1920年代才从一种“高跷”歌舞转变为有行当、有舞台的“高台曲”,不若豫剧自清末以来走过大江南北的发展,经历过多种艺术形式的融合、文人介入的“雅化”,以及1940年代在晋冀鲁豫根据地参与抗战工作的淬炼。曲剧是来自民间生活的小戏,戏词口语化,多用本嗓,所以易学易唱;抗战期间曲剧艺人曾经流亡南阳地区结成职业班社,得以学习南阳的“大调曲”,丰富了唱腔,也扩展了流传区域。但曲剧艺术的更大进步,乃至在全国知名,却与《卷席筒》有关,准确地说,与《卷席筒》在1950年代戏曲改革中的成功改编有关。
1951年开始的全国性戏曲改革“改人”、“改制”、“改戏”。1954年登封县文化馆接收赵保和文村戏班儿,正式成立登封县曲剧团。不到三十岁的团长何国正与编剧李国章两人开始酝酿改编《卷席筒》,1959年也逢作家李准到登封体验生活,对这部随着剧团上山下乡不断演出不断改编的戏十分欣赏,“仓娃起解”中那段“再不得摘酸枣把嵩山上,再不得摸螃蟹到黑龙潭,再不得……”据说就来自他的修改。此后,在河南人民剧院的成功演出和电台的传播,使得《卷席筒》在中原地区家喻户晓。1961年演员王善朴到北京参加“全国文艺工作会议”,时任文联主席的曹禺特意跟他提及《卷席筒》应“推广”。这就有了拍电影之议,1964年,谢添主导的摄制组甚至就要开拍了。
于锋《说说不一样的曲剧名剧<卷席筒>》(曲剧吧)这样回忆:
1964年全国“小四清”运动开始,导演谢添受到冲击。何国正曾致信谢导,谢导也表示到秋季摄制组就来登封。但因种种原因拍电影的事最终未成现实。随后,文化大革命开始,《卷席筒》戏被定罪,指责戏中有段苍娃的唱词是:“奉母命小南庄前去讨帐,讨回来百两银,交与爹娘,这一次的生意有了指望,与二老商量商量跑趟洛阳。”说苍娃参加讨帐,放高利贷,苍娃是地主羔子,剧团是为地主羔子歌功颂德。1967年12月登封何国正以及县曲剧团的其他领导和演员均被关在牛棚里反省,并多次挨打、游街。就这样剧团被解散,《卷席筒》戏也被冷落下来。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文艺得到了复兴,《卷席筒》戏又有了希望。但原登封县曲剧团的大部分演员都被调到开封地区曲剧团,也有一部分去其它剧团或洗手不干了……1979年初,郑州市曲剧团开始排练曲剧《卷席筒》,并在郑州各大剧院相继演出。由海连池演苍娃,使《卷席筒》大大走红。1981年由西安电影制片厂摄制的曲剧《卷席筒》系郑州市曲剧团演出……
从文革激进逻辑看,这部戏的“不正确性”是明显的。戏中设定的唯一之“恶”是赵氏,不仅“地主羔子”小仓娃是正面形象,地主曹林也是远近闻名的“善人”,受贿的县官在这里也不是直接的控诉对象。有意味的是,在建国初期的“戏改”中,这似乎没有那么“不正确”。《卷席筒》是作为一个(包含了旧意识的)家庭伦理戏铺陈的,却可能包含着建设新文化所需求的民间根底。
戏中人的言语举止、幽默深情,无不来自日常生活。伦理与亲情,以一个家庭的人伦悲剧、以小仓娃这个纯真少年的“无条件的仁义良善”来表现,这个“无条件的仁义良善”,实则是对超越财产、出身、血缘的情义的追求:小仓娃不求曹家的家产、不随母亲的贪婪、愿为没有血缘的兄嫂侄儿交托性命。这在今天或许被认为是底层道德的一种高度理想化的表达,在刚刚经历过革命的那个年代,却是许多人从革命中淬炼的真实人生。我那小时候随父乞讨山西的姥爷,1937年葬父参加了八路军、1950年代回到老家煤矿当工人、娶了我那拖儿带女的姥姥,的的确确是这样一个小仓娃。
不管李准和曹禺对《卷席筒》的肯定有怎样的具体意涵,都显示着1950、1960年代戏曲改革是接地气的,也是开放的。这是有历史延续性的,对旧戏的改造,在抗战时期根据地的文艺工作者譬如赵树理那里,就非常自觉。晋冀鲁豫根据地的豫剧团队参与抗战宣传的经验中,也有丰富的实践。建国后的许多文化工作者,有着这样的实战经验和真诚信仰,也因此,他们对《卷席筒》的赞赏和重视,或透露了文艺改革的一种想象:革命是可以跟传统的价值、伦理,构成一种充分结合的文化形态的。
#p#分页标题#e#说起建国初期到文革的文艺,我们习惯强调1962年以后阶级斗争的影响,阶级斗争的强调,确实对时代影响很大,《卷席筒》的电影在1964年终于没能开拍;但只强调阶级斗争对这一时期文艺的规定性的话,可能会忽略另外一些历史经验在知识和思想上的意义。《卷席筒》便提示着:戏改曾有相当的努力,不但对人民的情感需求,也对传统的价值心理有充分的面对。这其中,未必不包含着一种立足于建国后社会生活的、建构人民的“新文化”、“新政治”的可能。至于后来,很可惜地,戏曲大全,这种文艺上的努力怎么随着一场又一场政治运动僵化?“文革”也是对“新文化”、“新政治”的追求,但是怎样丢掉了此前这些富含活力的探索?只剩下了“八个样板戏”?今天对“八个样板戏”的探讨,又该如何与建国初的戏改做历史连续性的对话呢?
三、
1981年,西安电影制片厂拍摄、海连池主演的《卷席筒》上映后,一定是大大超出了中原地区“推广”了。我的生于江苏的好友玲玲说,小时候这部戏在露天电影院她可“看了一遍又一遍!”我们这代城里长大的孩子,已很少看到外台戏,但赶上戏曲电影的黄金时代。电影《卷席筒》之后,又有了电影《卷席筒续集》。财主曹林仍是个“大善人”;叔嫂情表现得活泼、动人而不失度——因为小仓娃是个憨少年!我老爸说,那时候很多剧团都演这个戏,常常唱叔嫂的两个人是“哭着唱”,我知道,做观众的他们也是“哭着看”的啊。
(荡开一句,文革后这部戏的重新红火,人们那样在“无条件的仁义”和相互承担的情感中放肆流泪,是不是也包含着一种创伤抚慰的需求呢?对文革作为政治、经济民主的设想有待重新认识,而对其具体过程中的问题,特别是人与人的关系、社会伦理的“大变局”,或也需要在“伤痕文学”的模式之外,做更历史化的反思。)
小仓娃这样伴随了我们几代人的记忆,海连池也至老活跃在乡村、工矿和荧屏的舞台上。
这一天,我看到他在一个晚会上唱《卷席筒续集》的一段视频——《小仓娃我生来灾星重》。老先生大约快七十,光头,无妆。一开口,我整个人都被震住。他的声音岂止中气十足,实在每一句都浸透了对生活的理解和情感。单声音,就可以勾魂摄魄了。而再听一遍,他唱出的每个词,都“是其所是”:他的“哎呀”让人心悬,他唤“亲娘啊”,人也如晤亲娘,并且同感他们分离的痛。当他唱着“三天两头上法绳”、呼唤“哥嫂可知晓”时,没有化妆的老人脸上,依然有着1981年的小仓娃的表情,鼻翼微张,挚情憨憨。从泪光晶莹的圆眼睛里你看到:小仓娃还是个少年!
海连池先生2012年,71岁过世。他晚年的生活一样经历了戏曲市场化后的诸多困境,他曾组织文化公司,做生意失败,名声一度被冒用。但老先生的担当,印证了从老年小仓娃眼睛中可以看到的,未失的赤子之心。
也是这天我邂逅了一则新闻报道:广州天河区,有一群来自河南周口太康县的豫剧老艺人,他们都是当年剧团的红角儿,几年前开始带着写有“因剧团解散,老艺人还乡务农,经文化局批准到外地旅游卖艺”的麻布袋,来到广州街头卖艺。收入无多之外,常遭城管驱逐。
心酸的不只是这群老艺人的处境——想想海连池在年近七十唱小仓娃、马金凤七十七岁唱“穆桂英挂帅”的精湛技艺和活泼精神,这群在街头用扩音器唱着随时会被中断的、碎片化的戏的老艺人,让人痛惜;由此还可以想象的,是他们不得不远离家乡的卖艺,是加入了村民外出谋生的大军而已。乡村已无戏,也没有了看戏的人。
我一度因为十几年来河南电视台《梨园春》戏曲节目(以打擂台比赛形式)的红火,以及《卷席筒全传》、《程婴救孤》这些“精品大戏”的强势打造和宣传,觉得豫剧在河南依然是有着强大群众基础和未来的。幻觉因此打破了。《梨园春》的红火除了群众基础,恐怕更是因为擂台比赛、草根成名的刺激,它是娱乐“消费”的一种。在政府文化工程扶助或商业投资下的“精品大戏”,明确导向是拿奖、“走向国际”。戏曲不再承担创造文化政治的责任,戏曲与人的亲密关系也远去了。
#p#分页标题#e#重省戏曲改革的经验,映照河南地方戏近三十年的困境与乡村的凋敝,更为心酸:到底是戏曲失去了观众,还是属于人民的戏曲、人民创造文化的空间,被剥夺了?
(不是戏剧研究者,也没有对豫剧团的兴衰做过调研的我,被五一劳动节无意间看到的新闻报道刺痛,写下这篇未及深入的札记。希望能引出对问题的一些讨论。也希望未来,自己能就此做点更切实的。)
2015年5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