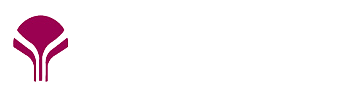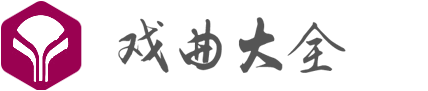一、传奇、乱弹之分立
元明清时期,文人戏曲与民间戏曲有明确分野:前者以文人为主要创作力量,作品形式“高雅”,主要体现文人的思想感情和艺术旨趣;后者以艺人为主要创作力量,作品形式“通俗”,更多体现普通人(主要为民众,也包括不免于“俗情俗趣”的其他阶层人士)的欣赏需求。这种差异是由两种创作者自身状况的不同造成的。简言之,文人在科举制下属于官僚预备队,地位高于平民,并掌握文化工具,而且文人制曲作剧的主要目的是“自见才情”,即展露文才和寓托情志,他们也主要是在高雅之士的小圈子内寻求知音,而不会取悦圈子以外的“俗人”。艺人属于贱民阶层,地位甚至低于平民,他们从事演唱和创作是为了谋生,因此他们的作品必须努力适应市场上“广大观众”的喜好,以贏得最大的观众面。再者,文人为了展露才情,创作上常常不避苛难(如填词制曲遵奉格律),而且可以“十年磨一剑”,作品力求精致。艺人则受自身文化水平限制,又迫于市场压力,创作只能主要采用“短平快”方式,常常无法精雕细琢,作品形式也必须不断追新逐异。两种创作者自身状况如此悬殊,文人戏曲与民间戏曲必定在品性风貌上呈现巨大差异。
戏曲史上的文人戏曲,主要有元杂剧和明清传奇两个大类。元杂剧也以文人为主要创作力量,但限于当时诸方面条件,元杂剧在艺术上的发展并不充分,对文人戏曲独特品质的体现也不全面。明清传奇则是文人把控最全面、作品体现文人特征最充分的戏曲形式,因而是文人戏曲最典型的代表。民间戏曲在宋元明时期也发育不充分,如宋元时的戏文(南戏),按照徐渭《南词叙录》的说法还属于“村坊小伎”,又如明代民间俗戏(也称南戏等,唱余姚腔、弋阳腔、青阳腔之类俗腔),祝允明《猥谈》的形容是“极厌观听”“直胡说耳”。直到清代乱弹兴起(主要唱梆子、皮黄等腔),民间戏曲才可谓全面成熟,因此乱弹可说是戏曲史上民间戏曲最大、最典型的代表。这里先将传奇与乱弹略作对照,以说明文人戏曲与民间戏曲在品性上的显著差异。
传奇首先注重剧曲文本,用今天的话说便是重视“剧本文学”。其中对曲牌文辞尤其看重,不仅讲求辞藻典丽、情致深婉,而且填词遵守格律,以“难能”为可贵。乱弹则更注重场上的“唱念做打”施展,“剧本文学”则不甚用力。因此乱弹剧本大都粗简而处理自由,唱词常常是上下句“顺口溜”,词意不通等情形也时有所见,与文人之作的精致优雅不可同日而语。内容方面,传奇多写才子佳人及忠臣义士故事,常有很深的情感蕴藉,其中的优秀之作也有很高的精神境界。乱弹则题材领域极广,故事情节丰富生动,人物千姿百态,对人情也有淋漓尽致的表达,但意识内涵常显得单薄,思想难以超越“忠孝节义”的高度。
音乐方面,传奇主要以风格清雅的水磨昆腔演唱。该唱法强调“字清、腔纯、板正”,即字音务求规范而清晰,腔调保持纯净,板拍严格遵循规范。而且演唱气度“全要闲雅整肃,清俊温润”,追求“气无烟火”的高远境界,这种“阳春白雪”的品质和风范自然不是民间俗唱所能企及。乱弹诸腔大都形式粗朴,处理不拘一格,腔调花样百出,音乐感染重于文字刻画,情感表达务求痛快淋漓,这些都与水磨昆腔形成鲜明对照。再者,传奇的曲腔结构属于“曲牌体”,常常重“曲”轻“戏”,一部传奇的曲牌数量可以多至数百,剧情结构却常常松懈,场上演唱时可以催人入睡,因而不少剧本始终停留于“案头”。乱弹则以“板腔体”为主,上下句滚动式的唱腔舒卷自如,使用灵便,“曲”在“戏”里如同鱼游水中,唱、念、做、打等手段的结合也十分灵活多样,视听效果往往显得丰富、生动。
#p#分页标题#e#传奇的场上搬演务求精雅,以士大夫所豢家乐(家班)的演唱为典范。文人亲自物色歌儿舞女,专聘教习进行训练,演出常在私家厅堂庭园或其他清雅场所举行,观赏者便是家乐主人和亲朋好友。这种小圈子演出常以“红氍毹”为代称,完全体现的是文人的艺术迫求。如张岱《陶庵梦忆》这样形容阮大铖家乐的演出:“讲关目,讲情理,讲筋节,与他班孟浪不同。然其所打院本,又皆主人自制,笔笔勾勒,苦心尽出,与他班卤莽者又不同。故所搬演,本本出色,脚脚出色,出出出色,句句出色,字字出色。余在其家看《十错认》《摩尼珠》《燕子笺》三剧,其串架斗笋、插科打诨、意色眼目,主人细细与之讲明。知其义味,知其指归,故咬嚼吞吐,寻味不尽。”文人也会延聘民间昆腔艺人(曲师)来为新作品编配唱腔和指导家乐演唱,还可召来民间昆班举行小圈子演出,但这类情形中艺人也必须唯文人之命是从。乱弹艺人则限于自身条件,他们的创作不可能像文人那样从容。乱弹的主要服务对象是普通民众,基本定位是“大众娱乐”。因而乱弹作品大都形式粗朴,不能做到精致优雅,与文人传奇的风貌相去甚远。在演艺市场上摸爬滚打,也意味着作品形式必须不断追赶时尚,创作方式必须灵活自由,不为清规成律束缚——这也正是“乱弹”得名的主要缘由(乱弹原是文人对民间俗腔俗戏的蔑称)。
总之,传奇的创作完全由文人主导,才子文笔加上秀婉典雅的“水磨”唱法和以家乐为典范的“红氍毹”式表演,使得传奇成为文人戏曲的典范形式。乱弹则纯为民间俗腔俗戏,其品性风貌与传奇形成一雅一俗、一文一野的鲜明对照,二者的差异几乎是“全方位”的。
关于“传奇”的界定,现今学界尚存在一些分歧。根据传奇之名在明清时期的使用情况,以及该时期内戏曲种类分衍的总体格局,笔者以为传奇主要应从文人来定性。首先,传奇之名当时便主要是指文人之作。例如吕天成《曲品》是一部评品传奇的著作,所录作品的时间范围从元末到明万历(有“旧传奇”“新传奇”之分),其中绝大多数作品出自文人之手(少量元末作品作者不详)。今天学界一般讲的传奇,实际上也主要是指文人之作。其次,从明清时期戏曲的种类分化情形看,文人戏曲(主要便是传奇)以“雅”为尚,与民间俗腔俗戏的差异十分明显,忽视这种差异,便难以看清该时期戏曲发展的主要走向和脉络。因此笔者认为传奇的文人属性应当强调(完整的称呼便是文人传奇),在传奇与同时期的民间戏(从明代俗唱诸腔到清代乱弹)之间应划出明确的界限。
还需注意的是,传奇是从文本到场上的整体概念,而不只是剧本(剧曲文本)。确有不少传奇文本停留于案头,未曾搬演,但它们并不是传奇的完整形式。上面说到的文人士大夫圈子内的“红氍毹”式演唱,才是传奇的整体呈现,因此不能因为当年的该类演唱不复得见便以为传奇只是剧本。例如《中国昆剧大辞典》将明清传奇定性为“明清两代南曲系统(包括昆弋腔、青阳腔、徽调等)长篇剧本的总称,或专指昆曲剧本”,恐欠周全。该辞典将孙鑛(《曲品》作者吕天成的舅祖)的“南剧十要”定性为“衡量昆曲剧本的标准”,也有同样的问题:“十要”中既有关于剧本、曲文的“要事佳”,“要关目好”,“要词采”等,也有关于搬演的“要搬出来好”,“要善敷衍——淡处做得浓,闲处做得热闹”,“要各脚色派得匀妥”等,故也不宜说它们只是衡量剧本的标准。
明代中后期及清代前期(15世纪后期至18 世纪前期)是戏曲史上的传奇时代——传奇在戏曲领域中地位最显赫,成就最高,不仅佳作众多,而且剧本文学达到了戏曲有史以来的最高水准,同时水磨昆腔代表了当时歌唱艺术的最高境界,表演方面也有很高的造诣。传奇由此在艺术上开辟了一片新的天地,将戏曲带上了一个新的高度,康熙中叶问世的《长生殿》《桃花扇》两部杰作成为传奇发展的顶点。然而雍正时传奇突遭釜底抽薪之厄:官宦之家“禁蓄声伎”,家乐趋于销匿,政治高压也使得本来热衷创作的文人几乎停笔;其后也有新作,但大都置诸案头。接下来剧坛的主盟者便成了昆剧。
二、昆剧对传奇的承续和“偏离”
#p#分页标题#e#昆剧从字面理解是“唱昆腔之剧”,其名初见于清嘉庆时,当时是指北京的徽班艺人在公众戏场上用昆腔唱的“剧”。如《众香国》评述徽班旦色艺人,分为六部,“每部首选,俱以昆剧擅长者冠之,重戏品也”。又如《听春新咏》记述徽班艺人郑三宝:“工于昆剧,偶作秦声,非其所好。《思凡》《交账》诸剧,淡宕风华,好声亦为四起,毋谓阳春白雪必曲高而和寡也。”后来昆剧便主要指民间昆班所演之剧,主要唱昆腔,也唱其他一些腔。20世纪50年代后昆剧成为一个“剧种”,其主体也是前代民间昆班所演之剧的延续(通常只唱昆腔)。
昆剧之名不仅出现较晚,而且清中叶后(延续至今)的昆剧已与明代及清前期的传奇有了很大的不同,不同的根本原因是清中叶起昆班的主要服务对象已不再是文人士大夫。昆班(也包括昆、乱兼唱的乱弹班)的演出通常是在公众戏场(戏馆、茶园、会馆、庙台等)举行,观众范围很广——其中可以有文人,但主要还是其他各色人等,而且数量最多的是普通民众。在这样的场合演唱,“上帝”自然是与文人士大夫很不相同的“广大观众”,故昆剧必定与完全按文人标准打造的传奇在品性风貌上有很大差异。传奇是以文人为“主人”:文人是创作的绝对主导,除了剧本出自文人之手,家乐的演唱也完全听命于主人(既是人身关系上的主人,也是艺术的主人),而且欣赏者也在文人小圈子内,因此作品体现的完全是文人的艺术理念和旨趣。这意味着昆剧与传奇在艺术定位上有着根本的不同。民间昆班也时常受雇在文人士大夫的府邸厅堂演唱,该种情况下艺人的演唱也必须满足文人的欣赏要求——与士大夫的家乐演唱很相似(民间昆班与文人家乐也多有交流,如家乐的教习常由昆班艺人担任),故那样的演唱仍然属于传奇的范畴。但在昆班置身公众戏场的情况下,适应更大范围观众的喜好是艺人生存的前提,他们当然不会仍然按照文人的标准演唱。
昆剧也与传奇有很多一致之处。虽然是以公众戏场为主要阵地,昆剧的艺术主体还是从传奇顺承而来,故与传奇仍有很多“重合”之处。昆剧对传奇的承续主要包含四个方面:一是大量作品直接袭自传奇,例如经典的折子戏大都由传奇的选出加工而成;二是主体声腔仍为传奇所唱的水磨昆腔,风格柔婉细腻;三是表演继承了传奇精致优雅的传统,台风严谨,常常一丝不苟;四是创作上延续了传奇推崇经典、注重规范的路数,很少自由创造和大幅度出新。例如乾隆时期苏州的集秀班:“集秀,苏班之最著者,其人皆梨园父老,不事艳冶,而声律之细,体状之工,令人神移目往,如与古会,非第一流不能入此。”这种精细而内敛的艺术格范无疑来自传奇。昆剧与传奇的界限常常模糊,甚至常被当成同一个概念,原因亦在于此。就称呼而言,这类昆剧与传奇的“重合”部分称为昆剧、传奇均无不可。清康熙时,文人圈内的传奇和民间戏场上的昆剧关系密切(亦分亦合),传奇仍为主导。但由于对文人的政治高压严峻,而且从雍正开始家乐被禁,故文人的创作热情骤减,传奇由此失去生存基础,急剧转衰。民间昆班将不少传奇作品搬到公众戏场上演唱,使传奇变成了昆剧,昆剧也顺势成为剧坛上的龙头老大。后来昆剧一直在戏曲界地位尊崇,用前引《众香国》的话来说是“戏品”高,与乱弹俗戏不在同一档次,也是因为继承了传奇的大量艺术成果。
但昆剧与传奇也有互相不能为对方包容的方面,可以说昆剧确立自己的独立地位的过程,就是与传奇逐渐“错位”的过程。出于对付公众戏场上“广大观众”的需要,昆剧艺人不可能完全按照文人的要求演唱传奇,他们的做法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所演唱的传奇进行种种改造,一是在传奇之外吸收或编创作品。下面分别说明这两方面的情况。
昆剧艺人搬演传奇作品时,根据公众戏场演出的需要,总要对文人原作进行不同程度的改造,其做法可说是“减法”“加法”并用。所谓“减法”,首先便是大大削减戏里的曲牌数量,以避免拖沓冗长,因为文人之作注重曲文铺陈,对于舞台演出来说,曲文常显得过“满”。所谓“加法”,主要是增入大量“戏”的成分,即说白、表演等方面的发挥,最常见的是加大丑、净、末等脚色的“戏份”,以增加场上的热度,追求生动的戏剧效果。文人(尤其传奇作者)对昆班艺人的这类“擅改”总是十分不满。如《桃花扇》作者孔尚任曾批评昆班艺人删减曲牌的做法:“各本填词,每一长折,例用十曲,短折例用八曲。优人删繁就减,只歌五六曲,往往去留弗当,辜作者之苦心。”还说到艺人在说白方面的“添油加醋”:“旧本说白,止作三分,优人登场,自增七分;俗态恶谑,往往点金成铁,为文笔之累。”又如梁廷枏《曲话》这样记述《长生殿》的演出情况:“《长生殿》至今百余年来,歌场舞榭流播如新。……然俗伶搬演,率多改节,声韵因以参差,虽有周郎,亦当掩耳而过。”显然,梁对昆班艺人擅改文人之作的做法十分鄙弃。
#p#分页标题#e#民国学者卢前对昆班艺人改造传奇的做法曾有简明扼要的归纳:“有案头之曲焉,有场头之曲焉。作者重视声律与文章之美,固矣。洎乎传奇渐入民间,顾曲者不尽为文士。于是梨园爨弄,迁就坐客,不复遵守原本面目,所谓场上之曲者,不必尽为案头之曲矣。……其于铺张本事,贯穿线索,安置脚色,均劳逸,调宫商,合词情,别有机杼,不同作者……盖南北曲之衰,以观众与作者相去日远,梨园遂设此折衷办法,亦一道也。”“案头之曲”是指文人原作,(梨园)“场头之曲”则指艺人的演唱,艺人的做法必然使作品的舞台呈现在相当程度上离开传奇原作。将《缀白裘》《审音鉴古录》等所录昆剧舞台演出本与传奇原作对照,也很容易看出昆剧与传奇会有什么样的差异。
在清中叶后盛演的昆剧折子戏中,昆班艺人改造传奇的做法有很典型、集中的体现。陆萼庭《昆剧演出史稿》“折子戏的艺术特点”一节列举了一系列昆剧折子戏(包括《狗洞》《春香闹学》《回营》《琴挑》《醉皂》《拐儿》等等),将它们逐一与传奇原作进行对照,显然对原作的“窜改”幅度已相当大。
除了改造传奇,昆剧艺人还创作或吸收了不少不属于传奇范畴的作品。例如《思凡》和《昭君》都是从民间弹唱改造而来的单出戏,与文人传奇已完全不沾边,明代曲集(如《风月锦囊》《群音类选》等)中已可看到它们的前身。清代《纳书楹曲谱》将它们归为“(弦索调)时剧”,并不把它们与真正的传奇或昆剧视为同类。《纳书楹曲谱》收录的此类“时剧”还有《醉杨妃》《芦林》《花鼓》《罗梦》《小妹子》等等,它们完全不是传奇,也不唱水磨昆腔。只是按照后来的笼统概念,凡是昆班演唱的东西都可以算昆腔、昆剧,故这类戏也常被视为昆剧。同理,全唱吹腔的《贩马记》因昆班演唱甚多,也常归于昆剧。
昆班艺人的上述做法,使得昆剧的面貌呈现出种种“混杂”特征。陆萼庭《昆剧演出史稿》曾指出昆剧存在“三大矛盾”;一是剧本与演出脱节,二是雅与俗杂交,三是观众层面不稳定(既有文人,也有民众)。这些“矛盾”正是来自昆班艺人对传奇的改造:剧本与演出“脱节”和雅与俗杂交,都是昆班艺人对传奇原作“率多改节”的结果;昆班在公众戏场上需要面对文人之外的更多观众,观众的构成也自然显得“不稳定”。
另外有些下层文人,甚至某些有编剧才能的艺人,也会为昆班编写剧本,剧本样式与传奇没有太大区别,但这类本子在编写时便会充分考虑在公众戏场上搬演的需要,因而其主要性质已属于“营业戏”,与典型的文人传奇也有重要差异。如明末沈德符《顾曲杂言》记述的情形:“年来俚儒之稍通音律者,伶人之稍习文墨者,动辄编一传奇,自谓得沈吏部(即沈璟——引者)九宫正音之秘;然悠谬粗浅,登场闻之,秽溢广座,亦传奇之一厄也。”清初李玉等“苏州作家群”的作品,市场取向很明显,也应是下层文人为昆班演出而作。
由于昆剧在舞台表演方面的发展,昆剧的脚色体制也与传奇的脚色体制逐渐拉开了距离。传奇的脚色通常为十一或十二种,包括正生、小生、外、末、小外、正旦、贴、小旦、老旦、净、副净、丑等。昆剧的脚色原先与传奇无异,但后来逐渐变化,清后期已形成一系列细分脚色,有“二十家门”之类名目,包括大冠生、小冠生、巾生、鞋皮生、雉尾生、老旦、正旦、作旦、四旦、五旦、六旦、净、白面、副净、二丑(副丑)、丑、老生、副末、老外等。昆剧这样的脚色规制,对传奇的脚色体制既有顺承,也有“偏离”。王季烈《螾庐曲谈》曾写道:“传奇中之主人,虽以一生一旦为多,而亦有不尽然者,如《邯郸梦》则以老生(即卢生)为主,《钧天乐》则以老生(即沈白)、小生(即杨云)为主。”其实在传奇《邯郸记》(汤显祖作)和《钧天乐》(尤侗作)中,主人公卢生和沈白都是正生,只是后来在昆剧舞台上卢生是老生。王季烈显然是把后来昆剧的脚色说成是明代和清初传奇的脚色,或者说是把传奇的帽子戴在了昆剧的头上,这种传奇、昆剧混而不分的做法,很容易造成认识的混乱。吴梅《顾曲麈谈》是将昆剧的脚色与传奇的脚色作了区分的:“传奇中脚色,总言之生、旦、净、丑。自明中叶海盐派盛行,继之以昆腔,而脚色遂繁。生有老生、官生、巾生、二生之名;旦有老旦、正旦、搽旦、小旦、贴旦之名;净有大、中、小之区别;惟丑则一耳。”还可注意的是:《顾曲麈谈》只谈传奇,几乎完全不谈昆剧,只是谈脚色时稍稍说到传奇与昆剧的不同。吴所著《中国戏曲概论》更是全然不提昆剧。显然,吴很清楚传奇与昆剧有重要差异,几乎不谈昆剧,是因为昆剧入不了他的“法眼”。
#p#分页标题#e#既然昆剧与传奇有显著差异,两个概念各自的内涵以及它们的关系便需要明确界定。昆剧如果根据字面理解为唱昆腔之剧,明中叶后用水磨昆腔演唱的传奇便已属于昆剧,但这只能说是广义上的昆剧。昆剧之名最初出现时是指公众舞台上的唱昆腔之剧(前已说到),其后又主要指民间昆班所演之剧(主要唱昆腔,也唱其他一些腔),这些又属于“狭义”的昆剧。20世纪50年代后作为一个“剧种”的昆剧,也无疑是“狭义”昆剧的直接延续。广义昆剧包含了用昆腔演唱的传奇,因而与传奇有更大的“重合”。狭义的昆剧则与传奇有明确区分:剧本由文人撰写,并且完全按照文人原作的要求来演唱(以家乐演唱为典范),是传奇;由民间戏班在公众戏场上演唱,对传奇有相当幅度的改造,又吸纳了传奇以外的不少东西,则是(狭义)昆剧。传奇完全按文人的理念打造,是文人自我表现、自我愉悦的产物,欣赏者也主要是文人;昆剧(狭义)则是将文人和艺人的创造融为一体,主要是满足公众戏场上“广大观众”的需要,这是二者在艺术定位上的根本差异。狭义昆剧中有很多成分来自传奇,广义昆剧与传奇的“重合”更多,故传奇、昆剧两个名称有时混用并不奇怪,但这不等于两个概念可以画等号。为了避免概念的含混,笔者以为在今天的称述中,昆剧一般还是用狭义为好(本文亦是如此)。
将传奇改造为公众戏场上的昆剧,主要好处是拉近与“广大观众”的距离,这样昆班离开文人还可以在市场上讨生活。但这样的改造也必然带来一种缺憾,便是“浅化”传奇的内涵,甚至降低原作的精神高度。例如现今有研究者讲《长生殿》,好就好在把李隆基、杨玉环写成了一对才子佳人(而不是帝王妃子),意思是李杨与那场安史之乱的干系不必理会,(经过这样的切割)两人的恋情完全纯真无瑕并值得倾情歌颂。笔者则以为这种讲法是忽略了传奇与昆剧的差异。从头到尾细读传奇原作,很容易感受到洪昇固然为李、杨之恋的破灭而深深惋惜,但他并没有刻意淡化李、杨的帝妃身份,从而抹杀“弛了朝纲,占了情场”的风流天子对那场倾覆社稷、涂炭生灵的浩劫应该承担的责任。“逞侈心而穷人欲,祸败随之”是洪昇对“天宝遗事”的一种理性总结,这决定了他不可能对李、杨之恋持无条件歌颂的态度。昆剧舞台上的李、杨,确实常常近似一对才子佳人,戏曲网站,但这不应该“归功”于洪昇。昆班艺人主要是选取原作中一些表现李、杨情感纠葛的折子进行加工演出,在表演处理上也总是强调两人的“情真”,因而李、杨之恋与那场安史之乱的关联被大大淡化,恋情本身也显得十分“美好”。艺人的这种做法既与营业的需要有关,也与他们的认识高度有关,但这样的舞台呈现实际上已偏离传奇作者的本意。坦率地讲,把李、杨之爱看得无限崇高,无视他们的社会责任,这是对传奇原作思想境界的矮化。昆剧舞台上的李、杨与才子佳人近似,也说明昆剧与传奇在精神内涵上已有不小的距离。
#p#分页标题#e#当然,昆剧改造传奇的做法多种多样,其中也有不少优于传奇原作的做法。尤其是在加强“观赏性”方面,昆剧舞台上有很多精彩美妙的处理,体现了昆班艺人高超的创造才能。但总体而言,昆剧很难将传奇原作中最具深度和最高远的精神内涵充分展现于舞台,这是无可讳言的。还可举传奇《桃花扇》为例。这部曾经被梁启超誉为“蟠天际地之杰构”的史诗性巨作后来很少为昆班演唱,昆剧舞台上偶尔只能看到《题曲》等个别折子,不少论家认为这是由于原作存在缺陷,因而不适于搬演,例如吴梅便曾批评剧中缺少“耐唱之曲”“通本无新声”等。但笔者以为《桃花扇》之所以后来很少演唱,一个重要原因是寄身市场的昆班根本没有力量将这部传奇杰作中的宏阔场面和厚重内涵按照作者原意呈现于戏场。《桃花扇》本来不是为市场营业而写,昆班艺人对这样一部史诗性巨作进行“加工”也显然不易措手(就连李香君的形象也与昆剧舞台上常见的“佳人”有明显距离),故以昆班的搬演能力和市场的口味来衡量孔尚任《桃花扇》的高度,难免有“标准错位”之嫌。昆剧的场上风貌之所以与传奇的思想内涵有明显的距离,说到底是由前面说到的文人、艺人两种人的不同精神境界和不同创作取向决定的:两种人的自身情形十分悬殊,创作方面的追求也大不相同,昆剧与传奇的艺术品质如何能等同视之?
还可注意的一个问题是昆剧的历史应该从哪里追溯。一些研究者把昆山腔、昆腔、昆剧、昆曲几个概念画上等号(常能看到“昆剧又称昆腔,又称昆曲”之类的说法),从而把昆腔(昆山腔)的历史与昆剧的历史混为一谈。这样的做法不很妥当,因为声腔只是剧种的成分之一,而且不是最主要的成分。还有研究者把元末的顾坚奉为昆剧的创始人或奠基者,因为后来有某处记载说到昆山腔是由顾坚打造。但顾坚其人很“缥缈”(几乎无证可考),而且明前期记载中的昆山腔是一种俗唱(前引祝允明《猥谈》所斥“极厌观听”“真胡说耳”的俗唱便包含昆山腔),为文人所不齿,明前期的文人传奇用那样的土俗之腔来唱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当时传奇所唱之腔应主要沿自前代戏文)。眼前明摆的事实是,昆剧最主要的成分直接承续于传奇:明前期传奇已在昆曲文本创作方面取得显著成就,明中叶后水磨昆腔成为传奇的主要声腔,士大夫家乐也在场上演艺方面达到很高水准,这些成果都被昆剧直接承续下来,并成为昆剧的主体。民间昆班承续了传奇的大量成果,同时也对之有相当幅度的改造,它们的演唱在清中叶后被称为昆剧,至20世纪昆剧又被视为一个“剧种”——这样理解昆剧的来路,岂不更顺理成章?撇开现成的传奇(或只把传奇当剧本),而偏把元末的顾坚当成昆剧的创始人,是否有舍近求远、弃大觅小之嫌?
广义的昆剧,自然应该从昆腔用于演唱传奇算起(不唱昆腔的传奇无法说是昆剧)。如有研究者讲:“昆剧的形成是从魏良辅创制水磨腔开始孕育的……魏良辅创造昆腔之后,这个剧种尚未形成,真正山昆腔发展起来而形成这一剧种的时间,应当自梁辰鱼把用昆腔演唱的《浣纱记》搬上舞台时算起。昆剧这一名称,自本世纪初期才开始有人使用,最初只偶见于文字记载,口头传述还是长期用昆曲二字指这个剧种的艺术整体,直到五十年代,才逐渐习惯于以昆剧来称呼这个剧种。”当然,一定情况下昆剧用其广义不是不可以,只是不应忘记:昆剧的指义不论多“广”,都不能与传奇完全“重合”,因此两个名称在使用上总要有区分。《浣纱记》可以用昆腔唱,也可以用其他声腔唱,只要是按照文人的标准打造,便仍然属于传奇。因此为了种类概念的清晰,笔者以为昆剧还是用其狭义为好。上面这段话是把传奇称为昆剧,前引王季烈那段话又把昆剧称为传奇(把昆剧脚色说成传奇脚色),概念都显得含混。
三、昆剧趋近乱弹
昆剧对传奇的“偏离”,实际上是向乱弹靠拢。乱弹作为传奇的“对立面”,其服务对象是公众戏场上的“广大观众”,形式通俗、创作自由为其突出特征(前已说到),而昆剧“偏离”传奇的做法同样是通俗化和自由化。例如乾隆时北京的昆班保和部:“本昆曲,去年杂演乱弹、跌扑等剧。因购苏伶之佳者,分文、武两部。于是梁溪音节,得聆于呕哑谑浪之间……”;其“武部”尤近乱弹,如旦脚郑三官:“昆曲中之花旦也。癸卯冬入京,虽近而立之年,淫冶妖娆如壮妓迎欢,令人酣悦。台下好声鸦乱,不减畹卿初至时。尝演《吃醋》《打门》,摹写姑妇春情亵语,觉委鬼之《滚楼》不过阳台幻景,未若是之既雌亦荡也。”又如清后期北京徽班编演的《盘丝洞》《天水关》等,研究者称为“昆腔俗本戏”——“为了迎合当时观众的欣赏习惯,由演员套用昆曲牌子演唱俗词”,除了腔调,已与乱弹没有多少区别。再如陆萼庭《昆剧演出史稿》所记清后期上海的昆班,所演包括“新编”灯彩戏、吸收自水路武班的戏、玩笑色情小戏等,并越来越多与京戏合演,其路数已与乱弹无异。该书后附“清末上海昆剧演出剧目志”中的小本戏、新戏、灯戏、时剧(包括高腔、吹腔、武班戏)和从京戏班吸收的戏,都和正路昆剧大不相同,而且其中不少就是乱弹。不少地区还有所谓“草昆”,更常常与乱弹打成一片,仍然以“昆”为称是因为还是唱昆腔(或为昆腔的变异),加一“草”字则表明那样的昆腔早已通俗化、自由化,与注重规范、品质优雅的水磨昆腔已相去甚远。
#p#分页标题#e#昆剧原为文人传奇与艺人创作混融、“折衷”的产物,其中包含着高低不同的层次,高层与传奇“重合”,低层又与乱弹难分难解,上、下之间跨度颇大。前引陆萼庭《昆剧演出史稿》所述昆剧“三大矛盾”——“剧本与演出的脱节”“雅与俗的杂交”“观众层面的不稳定”,都体现了昆剧在传奇和乱弹之间“游移”。昆剧一方面与传奇存在一脉相承的关系,因此总体品位高于乱弹;一方面出于市场打拼的需要,不少做法又与乱弹难分难解,有时如出一辙,有时只是五十步与百步的距离。总观清代前、中叶剧坛形势,最需注意的是传奇、乱弹的“二元对立”,以及昆剧在传奇和乱弹之间的“游移”。传奇与乱弹品性迥异,艺术上几乎完全背道而驰,形成了清代戏曲的“两极”。昆剧则大体居于传奇、乱弹之间——总体来看既不像传奇那样“阳春白雪”,也不像乱弹那样“下里巴人”,实际上是个“中间环节”。下面是对三者关系的一个简单图示(只是简单示意,图中块面不能准确体现对象大小):
从青木正儿起,戏曲史家们常常热衷谈论清代中后期的“花雅之争”,但他们大都是将传奇与昆剧混为一谈,并把它们笼统视为乱弹的敌对阵营。笔者数年前曾有《昆剧之“雅”与“花雅之争”另议》一文讨论“花、雅”概念和所谓“争”的问题,同样未将传奇与昆剧明确区分。但根据笔者现在的认识,昆剧和传奇如果不能明确区分,“花、雅”关系(或者说昆、乱关系)就无法真正讲清。在传奇、昆剧、乱弹三者关系中,艺术品性问题和市场竞争问题也不宜混而不分。从艺术上看,真正与乱弹“对立”的是传奇,昆剧则与乱弹相近、相通之处甚多,可以说昆剧作为一个独立戏曲种类的存在,完全是在传奇与乱弹之间“左右逢源”的结果。从市场的角度看,传奇是文人圈子的东西,其生存层面和艺术追求均与乱弹相去甚远,二者实际上不存在“争”的问题。传奇销匿的根源也是在于文人自身状况的改变,而不是因为在市场上“争”不过乱弹。在市场上与乱弹发生碰撞的是昆剧(昆班),“广大观众”越来越喜欢乱弹,昆剧自然就会被冷落。
昆、乱关系还有另外一面也需要注意,即二者也常常“合作”。例如乱弹自我提升的重要途径之一便是向昆剧学习,同时昆班在一定条件下也会吸取乱弹的东西。还有不少戏班昆、乱兼唱(如前面说到的北京徽班),甚至同一部戏里昆、乱兼唱,此类情形中二者的关系更如同一个人的左右两手,它们之间更不存在“争”的问题。昆、乱同样靠市场为活,它们固然有种种差异,但“同质”之处也很明显,一定情况下“相辅相成”也不奇怪。
昆剧兴盛于清中叶,但其“老本”得自传奇,被视为舞台艺术重要进步的折子戏的锤炼,也显然是传奇局部成果的延伸和发展。在继承和发展传奇固有精彩的同时,昆剧的一些显著弱点也与传奇直接有关,例如艺术上自我绑缚过多,以致创新乏力,开拓不足,便与传奇注重规范和推崇“经典”的路数很有关系。昆剧中靠近乱弹的新戏倒有一些,如前面举到的《盘丝洞》《天水关》之类,但该类戏的编创只着眼于营业,不仅无法具备传奇的高度,自身也没有什么独特的成就可言。
#p#分页标题#e#乱弹在清前期尚不成气候,但在清中叶昆剧主盟剧坛时,乱弹迅速扩充势力,一方面从昆剧大量吸收剧目和艺术养分,一方面自己也大力开疆拓土。乱弹的起点很低,从艺术形式到作品内涵都显得高度不够,但乱弹的最大法宝是完全开放的姿态和充分自由创造的精神,因而作品产量极大,舞台艺术不断提升,总体上生气勃勃。至清后期乱弹终于横扫剧坛,打出一片自己的天地,成为戏场的绝对主宰——纯粹的昆班已完全无法在市场上与乱弹班争锋,乱弹却吸纳、融汇了昆剧的大量成果。这便是戏曲史上滚滚而下、喧腾不已的乱弹时代。乱弹时代的开启意味着传奇时代的终结,两个时代的更替是清代戏曲史上的一场最大变故。
在传奇和乱弹两个时代之间,昆剧更多属于传奇时代的余晖,却未能打造出一个独立的“昆剧时代”,原因是昆剧自身分量有限。昆剧折子戏既延续了传奇的部分精彩,又融入了昆剧艺人的独特创造,舞台艺术水准很高,但折子戏的格局终究不大。前面已说到昆剧对传奇的改造,好处主要是拉近与普通观众的距离,代价却常常是作品精神内涵的浅化和矮化。折子戏之外,昆剧在创新、拓展的广度上更显得有限,例如几乎看不到什么像样的新戏新腔。因此,尽管昆剧在剧坛上享有尊崇的地位,舞台艺术上也在一定方面有很高的造诣,但从总体分量和综合贡献来看(涉及新作品数量、市场占有份额和艺术上的开拓创造等),昆剧既无法与传奇相比,也无法与乱弹相比。昆剧尽管在传奇和乱弹之间“左右逢源”,但最终未能打造出一片全新的天地,只是在传奇时代和乱弹时代之间成为一种承上启下的“过渡”。当然,“过渡”二字并不抹杀昆剧的重要地位和贡献。昆剧以折子戏形式将传奇的不少精彩创造延续下来(尽管只是一些“片段”),并有新的加工锤炼,可谓功绩显赫。昆剧也为乱弹提供了很多艺术养分,而且为乱弹树立起很高的艺术标杆,因此也对乱弹的成长发挥过极重要的引领和提升作用,这同样十分难得。